蘇維埃建設初期列甯有關新聞事業的觀點——以俄共(布)代表大會的決議為中心
【内容摘要】十月革命勝利後,列甯發表過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建設的觀點,在俄共(布)曆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都有所體現。1919年,國内局勢得到鞏固後,俄共(布)八大《關于黨和蘇維埃報刊的決議》把工作的重點放到了貼近人民生活以及恢複重建等方面,強調要反映實際,加強與群衆的聯系,決議中還提出在堅持黨的原則的基礎上保證報紙的獨立性,對報紙的監督功能也做出了明确的規定。1921年,俄共(布)十大列甯在閉幕詞中談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媒體的本質,列甯對西方報紙的批評有着複雜的國際關系背景。新經濟政策實施後,蘇維埃報刊處于嚴重的危機之中,社會關系複雜化,各種社會理論和思想出現在出版物中。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做出了《關于報刊和宣傳》的決議,一方面要使報刊能夠引導和輔助經濟建設,另一方面意在鞏固政治控制和思想穩定。針對決議中禁止《真理報》刊登廣告的條文,列甯提出反對意見,并被采納,這次代表大會是列甯最後一次出席的代表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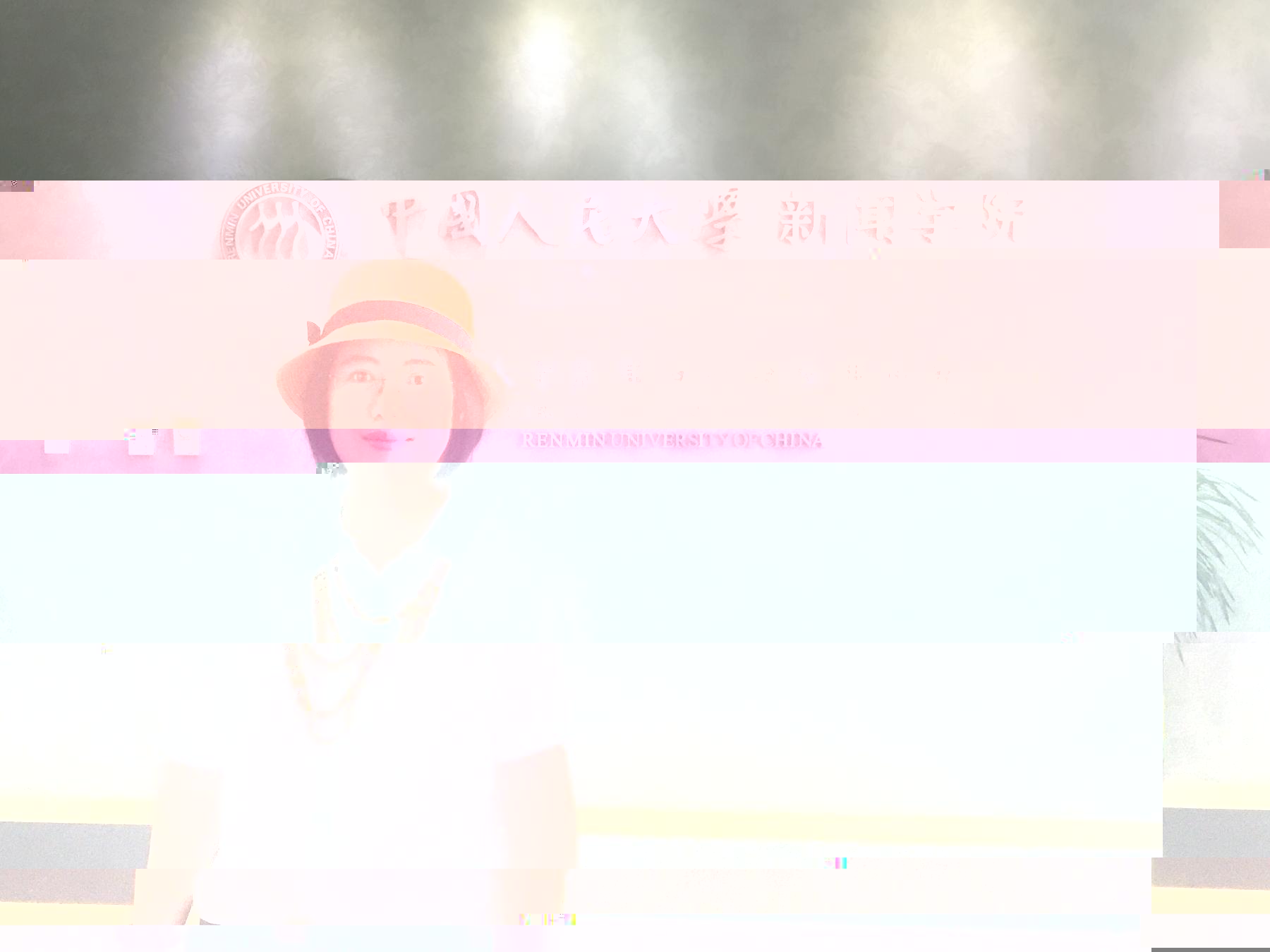
新聞傳播學界有關列甯的研究多集中于對列甯新聞思想的解讀,尤其是列甯關于革命時期無産階級報刊黨性原則及功能的論述是學界的研究重點,而對于蘇維埃國家成立後列甯關于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建設的思想觀點關注不夠。本文以俄共(布)三次代表大會有關報刊的決議為線索,梳理列甯在蘇維埃初期有關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建設的一些觀點。
一、 改善報刊工作、反映實際生活、加強與群衆的聯系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于1919年3月18日至23日在莫斯科舉行,當時正處于國内戰争時期。這次會議上,列甯認為,雖然“世界上所有的強國都反對蘇維埃國家”,但由于黨和政府所進行的巨大工作,在召開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時國内局勢已經大大地鞏固了。[1]正是基于這種對局勢有利于蘇維埃的判斷,《俄共(布)八大關于黨和蘇維埃報刊的決議》更多地把工作的重點放到了貼近人民生活以及恢複重建等方面。
該決議指出:“國内戰争時期黨的工作普遍削弱,十分有害地影響了我們黨的和蘇維埃的報刊的狀況。幾乎我們黨的和蘇維埃的一切定期出版物的共同缺點,就是脫離當地的生活,而且也往往脫離共同的政治生活。……完全刊載各主管部門和機關的各種指令和決議,卻不用所有這些材料彙編成地方生活的生動紀事。”[2]該決議認為造成這種缺點的原因,主要在于“黨的優秀的文字工作者都去參加政府工作,而報刊工作多半是由一些缺乏經驗的工作人員來掌握。”[3]
不難看出,當時的俄共(布)對報刊工作十分重視。在這一決議中,再次強調了列甯對于“報刊是宣傳、鼓動、組織的強大武器” [4]的基本觀點。對這一觀點的再次強調,與列甯對于當時蘇俄革命以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狀況的認識有着密切的關系。列甯指出:“以前我們是用一般的真理來做宣傳,現在我們卻是用實際工作來做宣傳。”[5]
在改善黨的和蘇維埃的報刊工作方面,決議中提出了一些創新的要求,力圖在堅持黨的原則的基礎上,保證報紙工作的獨立性。它規定黨委會給予編輯部政策指示并監督其執行,但是“不要幹涉編輯部日常工作的細節”,戰時書報檢查的範圍也應當嚴格限制在作戰和軍事組織性質的範圍内。[6]
決議對黨和蘇維埃報紙的監督功能也做出了明确的規定,“揭發各種負責人員和機關的犯法行為,指出蘇維埃組織和黨組織的錯誤和觀點”是黨和蘇維埃報刊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決議還賦予被監督對象辯駁的權利,它要求報道對象“必須于最短時間在同一報紙上做出認真的合乎事實的反駁,或者說明缺點和錯誤已經改正”。而如果沒有進行辯駁的話,革命法庭就對上述人員和機關進行起訴。[7]
決議最後還對地方報刊的工作以及黨中央報刊的黨建提出了要求,并再次強調各級黨組織要把最堅強、最有毅力、最忠誠的工作人員派去為報刊服務。
這一決議總結了俄共(布)在報刊實踐中的經驗教訓,是列甯對輿論監督功能強調的體現,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和曆史意義。
1950年4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中共中央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規定列甯《論我們的報紙》、斯大林《論自我批評及反對把自我批評口号庸俗化》、毛澤東同志《論自我批評》和《俄共(布)八大關于黨的和蘇維埃的報刊的決議》作為各級黨委和黨報黨刊的學習資料。決定的内容明顯受俄共(布)八大《決議》影響:“使報紙成為群衆的組織者、新民主主義的宣傳者和熱心的鼓動者,以及成為國家建設的戰鬥武器”“接近群衆,影響他們,做他們自覺的和領導的中心。組成巨網散布全國”“反映群衆生活、指導群衆行動”。
二、 列甯對西方報紙歪曲報道的批評
1921年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16日大會閉幕,列甯緻閉幕詞。在閉幕詞中,列甯較為集中地談到了外國媒體歪曲報道蘇俄國内情況的問題,揭示了資本主義國家媒體的本質。這篇發言同時反映了當時蘇俄所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世界範圍内不同制度之間的矛盾凸顯出來。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自誕生之日起即引起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極大恐慌與敵視。其中原因,除了政治制度的差異,經濟損失也是主要的考慮因素。蘇俄政府對私有資本的國有化侵害了西方發達國家在俄的經濟利益,因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而引發的這些矛盾拉開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态對抗的曆史序幕。
蘇維埃俄國在取得國内戰争的勝利後,工作重心轉向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召開為恢複國民經濟建設提出了具體的方案,決定從戰時共産主義政策轉向新經濟政策。
1921年3月1日至18日,俄國波羅的海海軍艦隊發生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事件。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開幕,七百餘名大會代表中約有三百人去鎮壓喀琅施塔得水軍起義。國外媒體和政治力量借此持續攻擊蘇維埃政權,列甯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閉幕詞中稱 “世界資本主義掀起了一場空前瘋狂的、歇斯底裡的運動來反對我們……”[8]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列甯批評了西方資産階級報刊對蘇俄國内局勢的歪曲報道與制造的大量謠言。
列甯指出:“這個運動規模很廣,計劃周密,說明它是由所有主要國家的政府精心策劃的一次行動。”[9]列甯在發言中詳細列舉了3月2日到3月14日各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媒體對蘇俄國内局勢的報道。西方的報紙大量刊載了肆意捏造的新聞,大意都在表明蘇俄境内局勢動蕩,布爾什維克的力量節節敗退。
列甯認為:“情況是非常清楚的。全世界的報刊辛迪加——那裡的新聞自由,就是99%的報刊都被腰纏萬貫的金融巨頭所收買——展開了帝國主義者的世界大進軍……”[10]。蘇俄當時的緊迫任務是改善國内經濟狀況,俄共(布)十大宣布即将實施新經濟政策。在大會上,代表們讨論了同美國恢複經濟貿易往來的議題。列甯在閉幕詞中講到:“包圍着我們的敵人進行武裝幹涉不行了,就指望叛亂。喀琅施塔得事件也表明了同國際資産階級的聯系。”[11]列甯認識到蘇俄的發展必須打破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隻想借遏制貿易的手段來改變蘇俄的體制。
十大閉幕詞中列甯對西方資産階級報紙的批評有着複雜的曆史背景和國際關系背景。1921年列甯對西方媒體的批評以及蘇俄轉向新經濟政策的決定,集中體現了蘇俄對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道路的探索。
三、新經濟政策實施後出現的報刊問題及解決
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讨論并通過了有關報刊和宣傳的決議。決議認為,蘇維埃和黨的辦報活動出現了問題,主要表現在報刊種類、發行量都在銳減,同時發行工作混亂;報刊遠離群衆,對地方經濟建設關注不夠,不能反映群衆的需求與要求;主要原因在于報刊主管單位的态度問題,地方黨委多半沒有堅決執行俄共(布)八大關于報刊的決議與俄共(布)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地方報刊的決議。決議還要求,黨員必須訂閱報紙,并将訂報視為義務。
“新經濟政策”實施後,市場重新恢複交易,部分行業允許私人企業經營。新聞業方面,私營出版社和合作出版社紛紛成立,其數量達四百餘家。1917—1919年,蘇維埃政權通過發布一系列法令,以查封、收買、沒收等方式逐漸取締了資産階級商業報刊和不同黨派的報刊。此時,重新啟動了私營報刊的出版。
伴随着國家對經濟政策的調整,各種社會理論和思想出現在出版物中。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俄共(布)十一大提出了報刊與宣傳的問題,經大會讨論,最終做出了《關于報刊和宣傳》的決議。針對社會上出現的思想問題,決議指出“在資本主義關系有了發展的基礎上,資産階級對小資産階級居民階層的影響,甚至對最落後的一部分無産階級的影響都不可避免地加強起來……黨應當千方百計地擴大和深入展開自己的宣傳鼓動工作。”[12]
在這一時期,蘇維埃報刊處于嚴重的危機之中。決議中指明了危機出現的原因,首先是印刷成本太高,蘇維埃報業辦報資金不足,造成報紙種類和發行量都在銳減;其次是報紙與群衆的聯系不強,對地方經濟建設關注不夠,不能及時反應勞動人民的需求以及地方經濟建設的情況;再次,報紙在堅持黨的政治立場方面不夠堅定;最後,發行工作中存在混亂問題。
決議認為,絕大多數黨委會沒有起到領導報刊的作用,忽視了報刊在社會活動中的重要作用,黨委會應該對報刊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負有主要責任。究其原因,大多數地方黨組織沒有執行1919年俄共(布)八大通過的關于報刊的八項決議,以及俄共中央關于改進地方報紙工作的指示。在這些決議和指示中,分别提到要重視對地方生活的報道,對經濟建設的報道,要加強與群衆的聯系等要求。
針對蘇維埃新聞業當時的狀況,十一大關于報刊和宣傳的決議要求:為了鞏固意識形态的穩定性,在報刊管理方面中央和地方的各級黨委組織要在今後比過去更注重報刊問題,應當加強黨對整個報刊的領導工作,每個黨委會都應當配備負責報刊工作的專職幹部;延續八大中關于報刊的決議,報紙内容不能脫離社會建設的實際生活,報紙内容應當能夠反映地方建設問題、群衆生活和工作,要有專門的報紙和版面用來反映農民問題;擴大訂戶,增加收費部分的發行量,給報刊以必要的物質幫助,采取措施保證黨和蘇維埃報刊的正常出版;在黨的省委會領導下,在部分大省保留獨立的共青團機關報,其他地區要在黨和蘇維埃的報刊上開辦青年專頁;注意同非俄羅斯民族地區的聯系,為非俄民族出版報刊和書籍。
決議中還強調指出,各省委會、區委會沒有設立報刊領導機構的應迅速建立報刊處;廣大黨員應該閱讀黨報,黨組織或黨員個人都應把訂閱一種黨報視為一項義務。決議重申,共産黨員不能參加資産階級報刊的工作,“隻有得到相當的黨委會的同意以後,才能作為一種例外情況去參加私人出版物的工作”。[13]
為了提高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工作的質量,決議中要求中央委員會和各級黨委會要注意,必須設立出版社,創辦黨的委員會雜志。決議中還要求“采取一切辦法來編寫和出版馬克思主義教科書,選派足夠數量的工作人員來做這一工作,把各地在這方面的工作協調起來。代表大會責成中央委員會采取措施在最近期間内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首先是出版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著作。”[14]同時,決議中贊同中央委員會要出版大量科學和文藝叢書的提議,意在加強對青年群衆的共産主義教育,具體工作由中央委員會協同共青團完成。
十一大閉幕後,按照《關于報刊和宣傳》的決議精神,各報做出了及時的改正,報紙的宣傳重點轉向了對經濟建設成績的報道。總之,俄共(布)十一大關于宣傳工作的決議緣起于當時社會政治出現困難的境遇,決議内容是對報刊的社會功能的加強,使其能夠引導和輔助經濟建設,并鞏固思想政治穩定。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發生了關于《真理報》能否刊登廣告的争議,會上讨論通過的《關于報刊和宣傳》決議中有禁止《真理報》刊登廣告的條文。列甯對此提出反對,認為黨報可以通過刊登廣告增加收入、維持其辦報經費,而不應該依賴于國家财政。列甯的建議被大會通過,禁止《真理報》刊登廣告的條文遂從《關于報刊和宣傳》的決議中删除。
兩個月後,1922年6月6日蘇聯人民委員會發布了《關于圖書出版事業總管理局條例》,宣布成立圖書出版事業總管理局(Главлит),整合了全國書報檢查機關的職能,但對廣告并沒有做出商業限制,隻是禁止政治上和意識形态上的非法廣告。1928年,斯大林宣布結束新經濟政策,此後三十餘年,蘇聯報刊上的廣告就隻剩下不多的科研、招生、招聘等科學廣告或文教廣告了,直到六十年代實行經濟改革才有所變化。1954年前後,中國新聞界掀起了全面學習蘇聯報刊經驗的高潮,其中就包括對《真理報》不刊登廣告的學習。1956年新聞工作改革後,才重新開始重視報紙的廣告業務。
注釋:
[1]伊格納切夫, 著, 烏蒙, 譯. 俄國共産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及其在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中的曆史意義[M]. 上海:新知識出版社, 1956. 5
[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蘇聯共産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一分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579-581
[3]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蘇聯共産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一分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579-581
[4]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蘇聯共産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一分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579-581
[5]人民出版社. 在俄國共産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于黨綱的報告&在俄國共産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于農村工作的報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 31-54
[6]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蘇聯共産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一分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579-581
[7]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蘇聯共産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一分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579-581
[8]《列甯全集》(第二版),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0頁。
[9]《列甯全集》(第二版),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0頁。
[10]《列甯全集》(第二版),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3頁。
[11]《列甯全集》(第二版),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3頁。
[12]《蘇聯共産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2分冊,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9頁。
[13]《蘇聯共産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2分冊,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03頁。
[14]《蘇聯共産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2分冊,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04頁。
【作者簡介】
趙永華,遼甯撫順人,新聞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教育部“中俄新聞教育高校聯盟”召集人。莫斯科大學新聞系訪問學者、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新聞系訪問學者。研究領域: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俄羅斯東歐中亞媒體研究、世界新聞傳播史等。出版專著《在華俄文新聞傳播活動史(1898-1956)》(俄文版«Русскаяпресса в Китае (1898-1956)»在莫斯科出版)、《中亞轉型國家的新聞體制與媒介發展》、《大衆傳媒與政治變遷——聚焦獨聯體國家“顔色革命”》,參與編寫著作教材20餘部,主持國家級、省部級、國際課題20餘項,在國内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170餘篇。目前從事的科研項目主要有: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蘇聯新聞體制變遷史研究》;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對外傳播戰略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俄媒體交流、戰略傳播與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話語權的構建研究》。曾獲第9屆中國人民大學優秀科研成果獎論文類優秀獎。2011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7年,獲第七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優秀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