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甯的出版自由觀述要[1]
【内容摘要】在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史上,列甯有關出版自由的論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對列甯出版自由觀的認識存在不小的偏差。本文試圖從思想史的視角,基于大量第一手的文獻,還原列甯的出版自由思想,進而從四個方面,即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的進步性、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的實質、無産階級出版自由的前提及無産階級出版自由的性質,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讀:“出版自由”從中世紀末直到19世紀,在全世界成了最偉大的口号。相對于封建專制,資産階級出版自由是一個偉大的進步。但是資産階級出版自由作為有錢人的自由的局限性也十分的顯著。無産階級的出版自由與資産階級的出版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隻有剝奪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無産階級出版自由才有實現的可能。但是它也不是一種絕對的,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而是一種相對的、在法律範圍内的自由。
【關鍵詞】 列甯 新聞思想 出版自由觀 新聞傳播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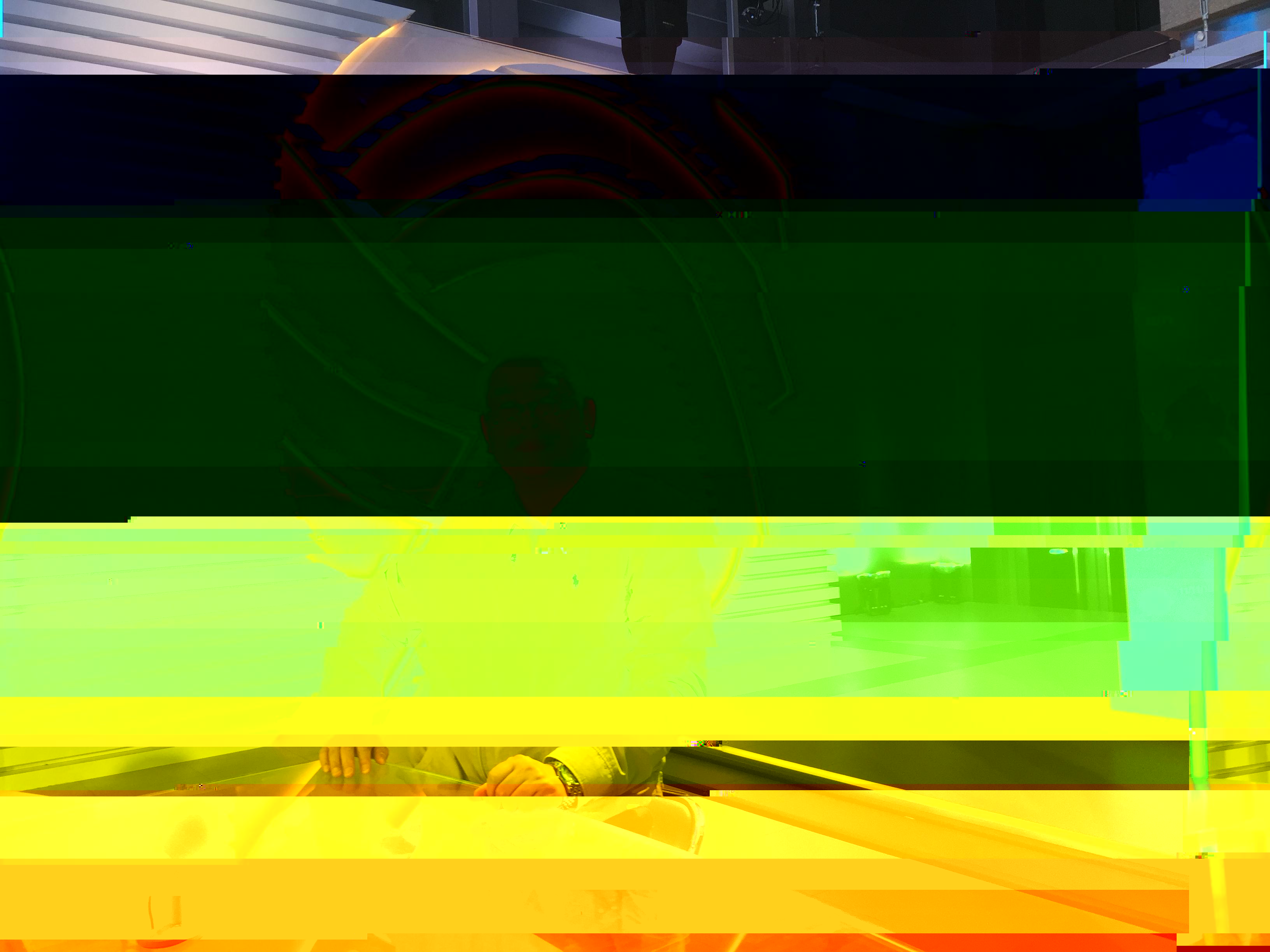
在世界新聞史上,無論是資産階級報業理論,還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說,都是以出版自由作為出發點的。出版自由不僅制約了報刊從業人員的活動空間,而且還決定了報道言論的真實程度。所以每個階級的報刊工作者,無不以争取、擴大出版自由為目标。在列甯的新聞思想體系中,對出版自由的論述也居于核心的位置。他認為,出版自由與言論、信仰、集會、結社、罷工自由一樣,屬于政治自由的範疇。其實質性訴求“就是全體公民可以自由發表一切意見”。要科學地理解出版自由問題,必須首先弄清楚是什麼樣的出版自由,“是法律規定的嗎?”“為了什麼?”“為了哪一個階級?”即自由的相對性、目的性和階級性。自出版自由口号提出以來,它一直屬于社會特定的階級,不是資産階級就是無産階級;沒有絕對的不受限制的自由,隻有法律規定的自由。自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基于這一認識,列甯的出版自由觀念主要是沿着兩個思路,即資産階級出版自由和無産階級出版自由兩個路徑展開的。
一、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的進步性與局限性
在列甯涉及出版自由的論述中,有相當部分是對于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的評價。此種評價包括肯定和否定兩方面。如聯系到列甯的新聞生涯,十月革命前,他對于資産階級出版自由大體上是肯定多于否定,而在此後,則是否定多于肯定。前期列甯對于出版自由的肯定,基本上是把它作為政治自由的一部分,作為現代文明的進步表現。在這個意義上,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自由、出版自由進行了高度的贊揚。特别是美國、英國、比利時、瑞士等國的民主政治,消除了中世紀的封建特權,公民們實現了政治上的權利平等,就是經濟上被剝削的工人階級亦“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會,自己的報紙,自己的議會代表。”政治自由早就成了人民的财富。1917年二月革命後,列甯對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的否定性評價雖然多于肯定性評價,但是仍然承認出版自由在曆史上的重大意義。在給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信中,列甯再次肯定:“‘出版自由’這個口号,從中世紀末直到19世紀,在全世界成了最偉大的口号。為什麼呢? 因為它反映了資産階級的進步性,即反映了資産階級反對僧侶、國王、封建主和地主的鬥争。”
和早期馬克思、恩格斯一樣,列甯對于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的肯定性評價與無産階級正在進行政治鬥争密切相關。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的确立,使無産階級得以利用報刊進行公開的政治鬥争。在專制統治下,封建統治者不僅控制了政權,而且還控制了出版,控制了思想,人民的怨憤、呼聲和強烈的願望無法公開表達。随着資産階級民主政治的确立,出版自由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至少從理論上看,這一權利的範圍及其主體是沒有什麼限制的,無産階級也是其中之一。在這個意義上,資産階級的民主制度和出版自由,可以說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出版自由作為一項基本人權,不是資産階級的專利品,而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大成果,是衡量文明開化的主要指标,是人類曆史重要的裡程碑。
另一方面,列甯對出版自由的肯定評價,還受到俄國特定的曆史傳統和政治現實的影響。直到19世紀末期,沙皇俄國仍是一個封建專制國家,與已經完成了資産階級革命,建立了代議民主政治的英國、美國、法國、瑞士諸國相比,不啻是天壤之别。在這些國家,出版自由得到了國家法律的保障,報紙被看成是第四權力,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可俄國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由于書報檢查制度的存在,一切出版物、一切報刊都處于奴隸的地位,任何一種非官方許可的出版活動,任何對政府的批評和不恭,都将被判為政治犯罪而受到嚴懲。列甯曾親身經曆過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環境:成長在專制統治的俄國,其革命活動、報刊生涯大部分則是在民主自由氣氛濃郁的西歐度過的。兩種不同的政治現實的鮮明對比,使列甯特别深刻地感受到了專制的朽惡和民主自由、特别是出版自由的可貴。
雖然在“二月革命”之前,列甯對于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的評價基本上是肯定的,持一種贊揚的态度,但同時他也意識到了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的局限性及資産階級對于出版自由的功利主義态度。在1905年俄國大革命時期,列甯就曾尖銳地揭露了“資産階級害怕充分自由和充分民主。因為它知道,覺悟的即社會主義的無産階級會利用自由來反對資本的統治。”二月革命推翻了俄國沙皇專制政府,出現了資産階級臨時政府與工農蘇維埃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的關系,由同盟者變成了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關系。“十月革命”勝利後,建立了無産階級自己的政權。資産階級的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被剝奪了。兩大階級的矛盾空前尖銳。為了推翻無産階級專政,煽動階級仇恨,俄國的資産階級報刊加入了國内叛亂和外國幹涉者的陣營。在這種情況下,列甯對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的認識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基本肯定轉向了基本否定。
列甯認為,資産階級出版自由就其實質而言,實際是有錢人的自由。固然,在資本主義社會取消了出版檢查制度、特許制、保證金制等專制控制手段,各黨派各團體均可自由地出版報紙。但是隻要資本主義私有制不變,隻要資産階級在經濟上的支配地位不變,“隻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紙張被資本家霸占,隻要資本還有統治報刊的權利(在世界各地,民主主義與共和制度愈發展,這種權力也就表現得愈明顯,愈厲害,愈無恥,例如美國也是這樣),這種自由就是一種欺騙。”
二、無産階級出版自由的性質與前提
根據列甯的論述,無産階級出版自由是一種真正的自由,它使報刊擺脫了資本的控制。因為無産階級的出版自由是共産主義者建立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沒有靠别人發财的可能性,沒有直接或間接使報刊屈從于貨币權力的客觀可能性,沒有任何東西能阻礙勞動者(或大大小小的團體)享有并實現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紙張的平等權利。”但是無産階級的出版自由也不是超階級的。在列甯看來,無産階級出版自由隻能是大多數人( 工農群衆) 的自由,其具體的表現,就是廣大的工農群衆可以免費地從蘇維埃政府和黨組織的各級報刊獲得消息,自由地參與這些報刊的業務活動,并且能夠通過這些報刊發表自己的意見,行使對社會組織及政府的監督權。至于在蘇維埃新的政治秩序下反革命的資産階級,是不配享有這種自由的。
在列甯看來,無産階級出版自由還是一種相對的、在法律範圍内的自由,而不是一種絕對的,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在無産階級專政下,怎樣能享有真正的出版自由?首先,必須擁護革命,“願意同工農一道忍受困難,為正義事業而戰”,并且“堅決保衛和支持蘇維埃政權”;其次,它還必須遵守蘇維埃制訂的各項法律,并且在這些法律規定的範圍内,從事采訪和報道活動;再次,它還必須服從蘇維埃國家出版局的行政管理。此外,報刊出版工作者還必須堅持起碼的技術标準,嚴禁粗制濫造,嘩衆取寵。對于那些亂七八糟、粗制濫造的報刊、書籍的責任者,應該把他們“關進監獄”。列甯還認為,出版自由固然是曆史上最偉大的口号,它能夠并且已經實際上促進了曆史進步,但是對于出版自由的作用又不能評價過高。特别是在社會主義制度草創、蘇維埃政權面臨着國内外敵人嚴重威脅時,切不可把出版自由當成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更不能如資産階級所标榜的那樣用出版自由來根治社會弊端。
列甯主張,無産階級的“出版自由就是使報刊擺脫資本的控制,把造紙廠和印刷廠變成國家的财産,讓每一個達到一定人數(如1萬人)的公民團體都享有使用相當數量的紙張和相當數量的印刷勞動的同等權利。”這一目标在資本主義社會顯然是難以達到的。隻有徹底地解放無産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推翻資産階級的統治,建立起無産階級專政,無産階級的出版自由才有實現的可能。
在列甯看來,無産階級出版自由的前提條件,就是剝奪資産階級的出版自由。因為不論是在十月革命前還是十月革命後不久,資産階級一直掌握着大量的紙張和印刷所,堵塞了無産階級通往自由民主的道路。所以必須采取措施剝奪了資産階級的出版自由權。
其一,設立報刊調查委員會和報刊革命法庭。前者成立于1917年,其主要責任是“調查定期刊物同資本的關系”在此基礎上,确定蘇維埃政府對資産階級報刊的基本政策。翌年,蘇維埃成立報刊革命法庭。該法庭的任務是審理利用資産階級報刊反人民的各種犯罪活動。對于此種犯罪活動,該法庭可以确定下列懲罰:扣款;進行公開譴責,即通過法庭所确定的方法将被查究的報刊作品公之于衆;在顯著的位置刊登判決書,或專門駁斥虛假的報道;停刊(包括臨時的和長期的)或停止發行;将被查究的印刷所或報社的财産收歸全民所有;剝奪自由;勒令離開首都、個别地區或者俄羅斯共和國國境;剝奪罪犯全部或部分政治權利等等。
其二,查封反革命報刊。 1917年十月革命不久,列甯便頒布了《關于出版問題的法令》。該法令規定,在新秩序确立之前,必須采取種種措施以反對“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報刊”,其主要措施就是查封。
其三,沒收或征用資産階級所擁有的印刷所和報紙。列甯主張像戰争時期對房屋、住宅、馬車、馬匹、糧食、黃金一樣,對印刷所和紙張也采取征用的政策。1917年12月13日,列甯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征用《交易所新聞》印刷所以及該所的全部房舍、機器、印刷材料、紙張和其它财産。”對于那些進行嚴重犯罪活動的報刊,則應由報刊革命法庭罰沒包括紙張、印刷所在内的所有财産。對于這些征用和罰沒而來的紙張和印刷所,蘇維埃政權将進行公平的分配。分配給國家、分配給在兩個首都獲得10-20 萬選票的大黨和一些比較小的黨以及任何一個有一定數量的成員或有某些人簽名的公民團體。這是實現無産階級出版自由的物質條件。
其四,清除反革命作家,流放、驅逐反動報人。在查封反革命報刊的同時,列甯還主張把“這些出版機關中凡有勞動能力的編輯和工作人員都動員去參加挖掘戰壕以及其它國防工作”。此外列甯還主張把那些“為反革命幫忙的作家和教授驅逐出境”,把那些反動報刊的主編、作者驅逐出境。
其五,蘇維埃政府對廣告的壟斷。列甯十分重視廣告在報紙經營中的作用。“這些廣告給出版這些報紙的資本家帶來一筆巨大的甚至是主要的收入。世界上所有資産階級報紙就是這樣經營,這樣發财,這樣毒害人民的。”但是資産階級廣告主絕不會把廣告投入給無産階級報紙。因此,列甯主張應采取切實措施使報紙廣告由國家實行壟斷。其具體做法是由國家公開宣布隻能在省蘇維埃和市蘇維埃出版的報紙以及彼得格勒中央蘇維埃出版的全國範圍的報紙上刊登廣告,而不允許在其他任何報紙上刊登廣告。在他看來,“這種辦法無疑是公平的。它對登廣告的人有很大的益處,也對全體人民特别是最受壓迫和最愚昧的農民有很大的益處,這樣他們花不了幾個錢或不用花錢就能拿到附有農民專刊的蘇維埃報紙。”而富人報紙則會由于失去廣告來源而大大削弱。在列甯看來,國家壟斷廣告的辦法不僅不會破壞出版自由,而且還會恢複和擴大出版自由。
此外,蘇維埃政府還可利用郵政系統為報刊提供發行服務。1918年11月,列甯簽署人民委員會法令,規定在俄羅斯郵電部門各個機構開設零售站和蘇維埃定期刊物發行站,出售蘇維埃和共産黨組織出版的報紙、雜志、手冊和書籍,接受這些報刊書籍的訂閱任務,給訂戶直接辦理郵寄刊物的手續。這樣一來,一方面減輕了報社的發行負擔,另一方面,又使報刊的發行範圍大大地擴張,提高報刊的發行效率,為廣大工農群衆購買訂閱提供了方便。
可見,無産階級出版自由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有其賴以确立的物質基礎的。列甯作為無産階級革命家,将無産階級出版自由建立在剝奪資産階級物質條件的基礎之上,而且在實踐上探索了實現這一目标的具體路徑。
列甯對出版自由的論述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今天奉為圭臬的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的重要來源之一。在國際國産主義運動曆史上,列甯的經曆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終其一生都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思想家。列甯則不然,列甯的前半生是革命者,是思想家,但是其晚年卻成了俄羅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這種生命的跨度使得列甯對報刊職能、使命及出版自由的認識,在其職業生涯的前後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其重要的原因,恐怕與思想家本身的角色轉變有直接的關系。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列甯也珍視出版自由,肯定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的進步性,盡其所能利用代議民主制下的出版自由,同時也剖析了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的虛僞本質。但是列甯的後半生,作為政治家大放異彩。他從鞏固政權、從國家治理的視角,來審視出版自由時,自然會理解自由的相對性、階級性和局限性。在思想史意義上,我們學習領會列甯的出版自由觀,會發現相對于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的出版自由觀更加适應今天中國的政治和傳播現實,對當今的新聞傳播實踐,也更有針對性和現實指導意義。
注釋:
[1] 本文系中組部、中宣部委托的“文化名家”及“四個一批”國家級人才計劃配套研究項目“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綜合改革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
[2] 列甯著:《怎樣保證立憲會議的成功》,《列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卷,第369頁。
[3] 列甯著:《莫斯科的祖巴托夫分子在彼得堡》,《列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卷,第273頁。
[4] 列甯著:《給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一封信》,《列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卷,第492頁。
[5] 列甯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卷,第44頁。
[6] 列甯著:《共産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1919年3月2-6日)》,《列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卷,第438頁。
[7] 列甯著:《共産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1919年3月2-6日)》,《列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卷,第439頁。
[8] 列甯著:《關于查封破壞國防的孟什維克報紙》,《列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卷,第425-426頁。
[9] 列甯著:《給瓦·瓦·沃羅夫斯基》,《列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卷,第426頁。
[10] 列甯著:《關于出版自由的決議草案》,《列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卷,第264頁。
[11] 列甯著:《關于出版自由的決議草案》,《列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卷,第264-265頁。
[12] 列甯著:《關于征用印刷所的指令》,轉引自楊春華、星華編譯之《列甯論報刊與新聞寫作》,新華出版社1983 年版, 第629頁。
[13] 列甯著:《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列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卷,第16頁。
[14] 列甯著:《緻費·埃·捷爾任斯基》,《列甯文稿》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卷,第225頁。
[15] 列甯著:《怎樣保證立憲會議的成功》,《列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卷,第368頁。
[16] 列甯著:《怎樣保證立憲會議的成功》,《列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卷,第368頁。
[17] 列甯著:《關于郵電部門出售蘇維埃出版物的決定》,載于1918年11月24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轉引自楊春華、星華編譯之《列甯論報刊于新聞寫作》,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630頁。
【作者簡介】
張昆,華中科技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領軍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劃評審專家、原教育部新聞傳播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原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年鑒編委會主任。第三批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國家文化名家”及“四個一批”國家級人才。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跨文化傳播中的中國國家形象建構研究”首席專家。主要研究新聞傳播史、政治傳播、新聞教育。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一般課題五項。獨著、主編專著、教材、文集二十多部,發表論文報告26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