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甯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蘇俄化——基于思想建黨的視角
【内容摘要】源自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經由列甯的創造性轉化,成為指導俄國革命的思想武器。列甯強化了思想建黨的作用,強調思想對于組織的先導作用和“腳手架”功能。利用報刊建黨,強化報刊的鼓動、宣傳、組織功能,鍛造革命黨組織,這種思想建黨模式是列甯的偉大創造。列甯強調報刊的黨性原則,一方面強調輿論的“一律”,但另一方面也對言論自由給予一定的空間和包容。
【關鍵詞】思想建黨 全俄機關報 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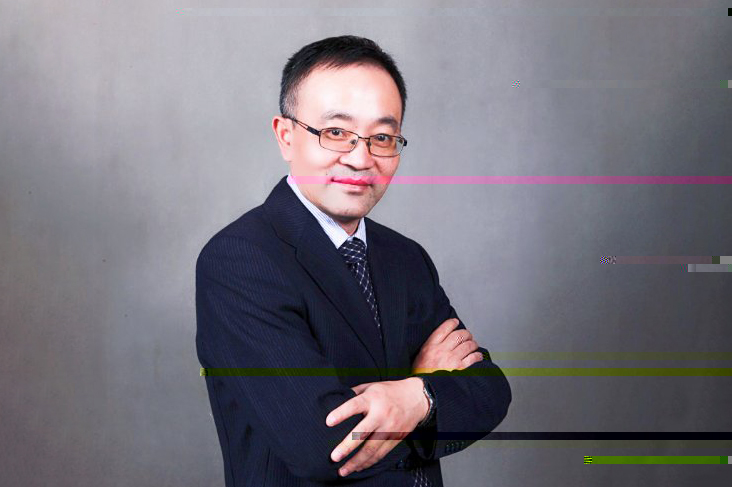
列甯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發動了一場刷新人類曆史記錄的紅色革命,開啟了人類曆史新紀元。成就這場革命一大重要因素是:先進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列甯的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列甯這裡強調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傾向,其立場雖是人類的、普世的,且當時歐洲資本主義處在上升時期,代表曆史前行的方向,代表先進生産力的發展方向,并向世界輻射,但馬克思恩格斯以敏銳的時代眼光和深邃的曆史洞察力,洞穿資本主義本質,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指導歐洲資本主義腹地工人運動的理論向導和思想武庫,同時,馬克思主義也從激越的無産階級解放運動中汲取經驗和教訓,豐富并發展自身的理論内涵。
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天下關懷,但離不開歐洲語境,基于歐洲語境的理論能否跨越時空,成為“他者”語境下的真理,尚需要實踐校驗。以列甯為代表的俄國革命家和理論家,在歐洲親曆火熱的共産主義運動,他完全有理由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原汁原味地移植到俄國。但是,列甯并沒有教條主義地照搬馬克思主義理論,坐等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以後,再發動無産階級革命,而是及時抓住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新變化、新機遇,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并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俄國革命情勢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催生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在俄國革命的複雜形勢中,抓住稍縱即逝的革命機遇,用革命的理論和果敢的行動,扮演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革命的助産士。
列甯在催動馬克思主義理論俄國化,并運用理論引領革命運動時,特别強調組織的作用。這既是列甯基于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存在不足的準确把握,同時基于對俄國革命條件存在的短闆的深刻洞察。列甯曾說過,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在列甯看來,無産階級在争取政權的鬥争中,除了組織,沒有别的武器。從當時國際語境來看,國際共産主義運動處于低位态勢,發動世界革命的條件顯然不具備。而從國内語境來看,在俄國發動工人運動和無産階級革命,這在馬克思主義經典革命理論中尚沒有明确的表述,甚至被認為是不可能的,按馬克思的判斷,共産主義者運動隻有在成熟的資本主義條件下,即在無産階級把革命條件準備充分之後,才有成功的可能。反觀俄國,它尚處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要讓無産階級革命早日臨盆,必須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創造一些有利條件。列甯作為俄國天才理論家和職業革命家,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以“組織”為革命支點,撬動俄國革命,且用理論鍛造組織,用思想武裝革命黨組織和無産階級隊伍,把無産階級革命引向成功之路。
思想建黨
列甯利用報刊建黨,強化報刊的鼓動、宣傳、組織功能,鍛造革命黨組織,這種思想建黨模式是列甯的偉大創造。在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動無産階級革命,超前的目标與滞後的現實之間存在巨大落差,為催生、催熟革命,列甯抓住組織和思想建黨這個關鍵,通過建立革命先鋒隊,打造一個職業革命組織,同時通過宣傳鼓動和理論武裝,把組織凝聚起來,鍛造成思想統一、行動有力的先鋒隊組織。要把組織有效凝聚起來,思想統一是必要的條件,但現實的困難在于:俄國早期工人運動和黨組織活動,思想的渙散、組織的渙散,存在嚴重的“小組習氣”以及小集團、宗派習氣,地方工作仍然是狹隘的“手工業方式”。在政治意識和革命力量甚為薄弱的俄國,俄國沒有歐洲式成熟的民主基礎,無産階級沒有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沒有議會鬥争的場所。要在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提前發動一場社會主義革命,沒有革命的報紙,決不可能廣泛地組織整個工人運動。
發動無産階級運動,須有革命先鋒隊的先知先覺,需要無産階級政黨領導工人運動從自發走向自覺。列甯指出,工人的自發運動是社會主義革命活動的一個必要前提,但它是革命的一個不充分的條件。真正的社會主義意識必須由它的代表——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灌輸到沒有定向的群衆運動中去。隻有一個由職業革命家構成的、由有獻身精神的知識分子傑出人物組織起來的、高度集中化的黨組織,才能保證社會主義意識在工人們中間發展,将他們的自發鬥争引導為有意識的政治行動。[1] 列甯強調向工人階級灌輸社會主義意識形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純粹自發性的工人運動雖然表明了工人同資本家的對立,但是工人還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隻能從外面灌輸進去,隻能從經濟鬥争範圍外面,從工人同工廠主的關系範圍外面灌輸給工人。而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和對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離,都意味着資産階級思想體系的加強。因此,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要:反對自發性,要使工人運動脫離這種投到資産階級羽翼下去的工聯主義的自發趨勢,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羽翼下來,并積極地對工人階級進行政治教育,發展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2]
因需對工人運動進行革命啟蒙,列甯提出了報刊的黨報原則和宣傳功能。源自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經由列甯的創造性轉化,成為指導俄國革命的思想武器。列甯強化了思想建黨的作用,強調思想對于組織的先導作用和“腳手架”功能。列甯指出,報紙的作用并不隻限于傳播思想、進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3]即是說,報刊功能不僅要具有傳播功能,還要承擔起組織功能。列甯提出,靠報紙并通過報紙自然而然會形成一個固定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從事地方性工作,而且從事經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員密切注視政治事件,思考這些事件的意義及其對各個不同居民階層的影響,拟定革命的黨對這些事件施加影響的适當措施。[4]列甯最重要的實踐創新即是建立有紀律的職業革命政黨。黨及黨的紀律和權威,是進行有效的革命行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5]列甯認為,群衆會不自覺地傾向于改良主義。群衆越多地參加到政治鬥争中來,就越有必要具備一個穩定的領導人的組織。因此,黨與群衆的關系是單向度的:通過鼓動和宣傳,黨努力提高群衆的階級政治覺悟。[6]黨員如果不參加一個黨的組織,黨就不可能成為一個有組織、有紀律、能戰鬥的工人階級先鋒隊,而隻能是像第二國際各國黨那樣的松散的議會黨。[7]統一思想是統一行動的必要條件。列甯與普列漢諾夫等人于1900年在國外一起創辦了《火星報》。他在創刊号上發表社論《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開宗明義:報紙的主要任務是在俄國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在1900-1903年間,《火星報》發表了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并且努力把各地的社會民主主義組織進一步聯合起來。
建立全俄機關報
針對俄國黨報報刊的“手工業方式”,列甯提出要辦“全俄機關報”。這是極富戰略遠見的政治傳播戰略。俄國地廣人稀,物理溝通成本甚高,即便以城市為中心展開革命宣傳和政治行動,也存在嚴重的“小組習氣”,存在小集團、宗派習氣,思想渙散和組織離心問題突出,對此,列甯意識到,強大的組織必須要有有力的紀律和思想保障,他提出要辦“全俄機關報”。為了克服這個缺點,為了把各個地方的運動合成一個全俄的運動,第一步應當是創辦全俄的報紙。列甯指出,我們需要的是全俄的報紙。我們需要的報紙必須是政治報紙。沒有政治機關報,在現代歐洲就不能有配稱為政治運動的運動。沒有政治機關報,就絕對實現不了我們的任務——把一切政治不滿和反抗的因素聚集起來,用以壯大無産階級的革命運動。假使我們不能夠用報刊上的言論來統一我們對人民和對政府的影響,或者說在我們還不能夠做到這點以前,要想去統一其他更複雜、更困難然而也更有決定意義的影響手段,那隻能是一種空想。無論在思想方面,或者在實踐、組織方面,我們的運動的缺點首先就在于自己的分散性,在于絕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幾乎完全陷入純粹地方性的工作中。創辦全俄政治報應當是行動的出發點,是建立我們所希望的組織的第一實際步驟,并且是我們使這個組織得以不斷向深廣發展的基線。[8]
用黨報作為“腳手架”,把組織連接成統一行動、反應有力的物質力量。這一方面需要強大的理論感召力,把組織中的成員一個個吸納、團結在黨的周圍,尤其是團結在黨的領袖的周圍。同時,還需要有剛性的約束,須有鐵的紀律作為保障,将不同的态度、聲音、行動統一起來,形成統一意志和行動。為此,列甯提出了黨報的黨性原則。要求黨報須有黨性,黨的報刊必須堅持自己的立場,不能把黨報辦成一個形形色色觀點簡單堆砌的場所。确定黨的觀點和反黨觀點的界限是:黨綱、黨章和黨的策略決議。列甯指出,對于社會主義無産階級,寫作事業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與無産階級整個事業無關的個人事業。無黨性的寫作者滾開!超人的寫作滾開!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産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 為了鍛造鋼鐵組織,須把思想幹擾降低到最低限度,把組織成員的思想統一到黨的目标上來,通過思想的統一打造強固的組織和有力的行動。
黨性原則與言論自由的關系
列甯強調報刊的黨性原則,一方面強調輿論的“一律”,強調組織紀律,但另一方面也對言論自由給予一定的空間和包容。對外,強調口徑、态度統一,對内允許有分歧和争鳴。對于前者,列甯批評那些在黨的組織内部呼籲“自由”、反對組織“束縛”的那些人。黨的組織在他們那裡是可怕的工廠;部分服從整體或者少數服從多數在他們看來是農奴制,他們一聽在中央領導下進行分工,就發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對人們變成小齒輪和小螺絲釘。在那些過慣了穿着寬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奧勃洛摩夫式的家庭式小組生活的人們看來,正式章程是太狹隘、太累贅、太低級,太官僚主義化,太農奴制度化了,太約束思想鬥争的自由過程了。列甯指出,言論自由是一回事,而黨的組織紀律性是另外一回事。尤其在革命鬥争最為激烈的時期,列甯強調黨報的黨性原則,強調黨報的政治鼓動和宣傳功能,強調黨報在無産階級奪權鬥争中的戰鬥性,無疑是具有曆史合理性的。
列甯的強調黨報的黨性擔當,但并不意味着黨報上一味追求整齊劃一,強調組織上的步調一緻,以犧牲言論自由和個人權利為代價,追求表面上的“一律”。列甯指出,絕不否認現存的分歧、掩飾或抹殺這些分歧;公開的鬥争可以一百倍促成牢固的統一。提倡機關報上“同志式的論戰”。關于個人的言論自由和黨的組織性之間的關系,列甯作了清晰的界定:為了言論自由,我應該給你權利讓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謊和寫作。但是,為了結社的自由,你必須給我權利同那些說這說那的人結成聯盟或分手。黨是自願的聯盟,假如他不清洗那些宣傳反黨觀點的黨員,它就不可避免地會瓦解,首先是思想上瓦解,然後是物質上的瓦解。在這裡,列甯把個人言論自由權利與組織結社的義務辯正統一起來,二者并不是本質性的矛盾。
列甯集理論家、宣傳家、革命家和活動家于一身,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處于低潮、國内工人運動水平處于低位的情勢下,創造性地利用報刊的先導作用,通過思想建黨,成功規避了俄國工人運動的先天不足,在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催生無産階級革命。這與列甯對于黨報的天才設計和創造性實踐密切關聯。正因有黨的報刊的超常發揮,開發報刊的宣傳、鼓動、組織功能,把思想和組織強有力地凝聚在一起,确保黨組織的戰鬥力。
注釋:
[1] 莫裡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第77頁。
[2] 鄭永廷等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态發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
[3] 列甯:《從何着手?》,《列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列甯:《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列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 莫裡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頁。
[6] 布蘭特利·沃馬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頁。
[7] 李慎明、陳之骅:《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第61、62頁。
[8] 列甯:《從何着手?》,《列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簡介】
張濤甫,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黨委書記,複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第十五屆上海市人大代表,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新聞傳播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新聞大學》主編。研究領域:新聞理論、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輿論學、政治傳播。在中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三百餘篇,其中CSSCI期刊論文100餘篇。出版《轉型與在場》《表達與引導》等著作多部,獲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上海市哲學社科優秀成果獎、國家教學成果獎、上海市教學成果獎等十多項。主持國家哲學社科重點項目、國家哲學社科重大項目子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教育部新世紀人才項目、上海市哲學社科項目等十餘項。